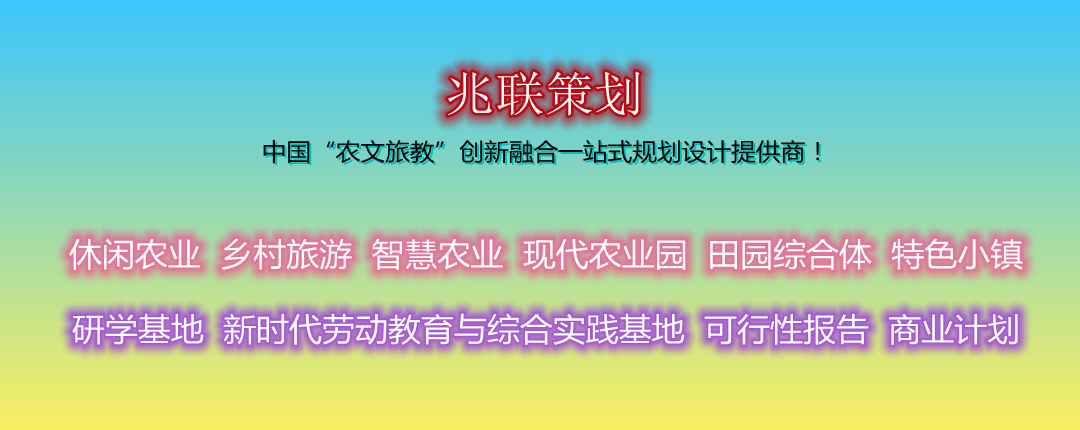新京报讯(见习记者 李谦锋)不知不觉间,曾经红火的农家院或者说“农家乐”,正在京郊一些村庄慢慢消失,坚持经营的,很多生意惨淡。
“农家乐”乐不起来了,其竞争残酷到了什么程度?在农家乐仍占主流的北京柳沟,“现在家家都去公车站、停车场等人多的地儿拉客,拉得慢了,事先预定的客人都能被别家带跑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萧条,几年来,太多经营农家院的村民因为生意冷清、加之自己上了岁数,关掉了“农家乐”,有人则直接去新开的民宿打工去了。
7月中旬,在记者走访的北京怀柔、延庆、房山等3个区、12个村子中,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的村庄,传统农家院的经营在普遍边缘化乃至消失,短短几年即被中高端民宿所取代。可民宿的高门槛,把多数原来的经营者拒之门外,“我们农民可没有这样的财力进行改造”。即便转型升级,随着社会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民宿这个行当是否要再步农家院的后尘,同样让不少民宿主有所顾虑。在这场产业升级的追逐中,经营农家乐的农民们将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民宿中的游客。李谦锋 摄
风光不再的农家院
2019年,56岁的杨全霞收获了一份全新的职业体验——民宿管家,“游客在网上下单后,就过来住,接待、清洁、退房等工作全是我一个人儿”。
杨全霞是怀柔区渤海镇苇店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她告诉记者,这两年外面来了不少投资商,在村里租赁当地村民宅院,有些就是之前的农家乐,然后改建成高端民宿,光苇店村就有6个。
苇店是京郊典型的山村,过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四周山上的栗子树。旅游业兴起以后,由于这里是市区去往慕田峪长城的必经之地,距慕田峪又仅有5公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旅游资源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投资商,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村里建起十几个度假村和饭店。
当地村民此前纷纷在自家院子经营起农家院,招待各地游客。杨全霞介绍,她家在2004年也开起农家院。“前几年生意非常火爆,我家10来间客房几乎都能住满,而且每天我还要做十来桌饭。”
“差不多2011、2012年以后,来农家院的客人就慢慢少了,今年我干脆就不做了”,杨全霞介绍,不止她家,村里之前的几十家农家院,现在都处在半歇业状态,“零零散散地偶尔来那么几个人,还不够折腾的”。
“这几年客人确实呈下降趋势”,六渡河村农家院店主樊丽萍说,六渡河依山傍水,是附近较早接待游客的村子。由于靠近主路,穿村而淌的怀沙河又经过樊丽萍家的门前,她告诉记者,在村里她家的生意“还算可以”。
“如今好多农家院因为生意不好都关了,有人把院子租出去,然后出去打工”,樊丽萍介绍,“我们也主要靠周末这两天,平时人也不多,而且只在旺季做半年,冬天游客更少,就不做了”。
樊丽萍说,她家的农家院只在旺季开半年。
游客都去哪儿住了
面对记者“游客都去哪儿住了”的疑问,杨全霞和樊丽萍均表示,住农家院的客人还有,但主力的年轻消费者都去了更为高端的民宿。
自家农家院停止营业后,杨全霞就到她家隔壁的民宿当起了“民宿管家”。在她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这家欧式精装、简约时尚的民宿酒店。
“人家这种高档民宿都是请设计师重新设计改造的,比起我们原来农家乐高档了很多。通过全新的设计,住客不仅住的更舒适了,还能欣赏到周边的山景。”杨全霞说。
服务水平提升了,价格自然也就高了。“之前农家院一间客房每天100块钱,这家民宿一间客房每天798元。这个小院有8间客房,包下这个小院一晚,需要4300元。”

杨全霞目前在这家民宿当“管家”,她表示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安静舒适的民宿。李谦锋 摄
“北京现在的年轻人收入高,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这样的民宿住得舒适,哪怕贵一点,他们也不再选择便宜的农家院了”,对于消费观念和习惯的改变,经营过农家院的杨全霞深有体会。
“以前我们自己住哪儿都行,但现在带着孩子出来玩,就想住得舒服一点”,“80后”游客王国兴介绍,这次他和朋友两家人租下了一处有3间客房的小院。“我们两家各自带着2个孩子,租下这处小院,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孩子能玩得开”。
游客黄燕、刘炼和王肃是金融公司的同事,他们这次住的小院带有3间客房、价格3980元/晚。“周末三家人约好一起来郊区旅游,郊区的环境非常好,能让人放松,住得也很舒适。”王肃说道。
性格开朗的黄燕告诉记者,“没想到厨房这么大,老板想得也很周到,连调料都帮我们准备好了,本来没打算做饭的我们也做起了饭”。
“孩子们来了也很开心,这不光有玩具,院子里还有个游泳池。”一旁正在收拾玩具的刘炼说,“人均600块钱,性价比很高”。

周末,几个朋友相约带家人去郊区住民宿成为一种流行。李谦锋 摄
十年前,很多北京人周末出游,看的是景,住宿讲究的是干净实惠,质朴的“农家乐”足以满足这个要求。而当“80后”普遍为人父母后,这一代人的“亲子游”观念似乎截然不同了。
做新药研发工作的刘希胜告诉记者,这次他和朋友两家10个人,其中有4个孩子和1个老人,以4680元租下了这处有6间客房的院子。“像家里一样舒适,家具、器具一看就不是那种地摊儿货,晚上还能烧烤,大人孩子都很高兴”,觉得性价比颇高的他说,“最重要的是清净雅致、环境优美,能一觉睡到自然醒”。

游客刘希胜表示,舒适的环境,人均500元左右,性价比很高。李谦锋 摄
“门槛太低”与“复制粘贴”终致农家院衰落
“农家院客源流向高端民宿,这种现象五六年前已有端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资源区划处处长陈奕捷表示,游客选择民宿已不只是解决住一晚的需求,还渴望得到更加舒适的享受,甚至在美学艺术上也有了更高追求,而这些是传统低端消费的农家院所不能满足的。
“可以说,即使没有民宿,农家院也会被乡村酒店、精品客栈等其他形式所代替”,陈奕捷表示。
目前,越来越多民宿经营者开始在硬件上实现升级改造,从房间内部装饰、具体用品再到外部环境都有所提升。相比农家院的简单乡村体验,如今“小而美”的民宿,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功能性都有很大升级。
“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桌子,做顿饭”,在民宿老板徐兴建看来,农家院的进入门槛太低。而这种低门槛,固然为产业的“复制粘贴”提供了便利,衰落却在所难免。
在以豆腐宴、火盆锅闻名的延庆区柳沟村,进了村便能看到十多个矗立在路旁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农家院编号、字号及电话等信息,最大编号已排到168号院。

柳沟农家院中吃豆腐宴的游客。李谦锋 摄
在柳沟,闫和花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都曾报道过她以农家院带领群众致富的故事。58岁的闫和花告诉记者,2003年政府扶持柳沟搞农家院,当时领到营业执照的有13家,但实际营业的只有她家和另外一家。
“后来几年,村里陆续都开起来了,全村一共有400多户,现在营业中的就有100多家农家院了。不光是我们村,其他地方都开起来了。农家院多了,竞争也就大了,有些农家院为了节约成本,降低了服务质量”, 闫和花告诉记者,如今的客人比两三年前“少了近一半”。
农家院的竞争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家家都去公车站、停车场等人多的地儿拉客,拉得慢了,事先预定的客人都能被别家带跑了。” 闫和花说,“本来村里集中开,有一定的集聚品牌效应,有个四五十家就可以了,但现在也太多了”。
柳沟67岁的张春荣就因为竞争太大,又年纪大了,在2015年关闭了自家的农家院。“我从2006年开始开,干了近10年,好的时候,一年能赚个五六万。后来农家院开得太多了,竞争压力太大,赚不了多少钱,我们年纪也大了,就关了”。

柳沟村路旁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农家院编号、字号及电话等信息。李谦锋 摄
农家院升级有哪些门槛
如果说门槛太低、复制性太强成为农家院发展的桎梏,高端民宿越来越受年轻消费者青睐,那村民能否通过升级改造,实现突围?
“改造民宿得花上百万,我们哪有这么多资金,再说就算借钱改造完之后,现有住农家院的客人留不住,新客源从哪里来,怎么赚钱?”樊丽萍无奈表示,“现在还能挣点钱,凑合着过吧”。
作为投资商,徐兴建表示,民宿算中高端消费,进入的门槛也相对较高。“也有一些农家院升级为民宿,但相对还算有限。因为民宿对选址、资金、设计、客源等因素都有限制,一般村民想要进入存在一定难度。”
“并不是所有农村都具备发展民宿的条件,选址上大有讲究”,徐兴建说,“我们2016年开业,在此之前考察了延庆几十个村子,最后只选择了3个村”。
“要能够形成聚落,在相对封闭的山脚下或山中景色优美、安静不喧闹的村子,最好能保留村子的‘原汁原味’,如果距离市里不太遥远会更吸引消费群”,徐兴建介绍,交通四通八达的村子,不能形成聚落,也不够安静,“一般饭店会喜欢这样的村子”。另外,如果村子太具有现代气息,遍布贴着瓷砖的新房,对游客也没吸引力。
在记者走访的北京怀柔、延庆、房山等3个区、12个村子中,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的村庄,传统农家院的经营在普遍边缘化乃至消失,民宿当道,以怀柔渤海镇四渡河、六渡河等几个村子为代表。而在游人如织的延庆柳沟,高端民宿仅有当地村民开设的一家。徐兴建告诉记者,“像柳沟这样的村子,虽三面环山,但交通较发达,又地处旅游景区,属于典型的‘过路村’,适宜开展餐饮,高端民宿选择在这落户需要慎重考虑”。
民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内涵和个性化,一般需要建筑、室内硬装、室内软装和庭院设计等4个设计师。“建筑设计和庭院设计大家比较熟悉,室内装修分为硬装和软装两种,硬装就是指吊顶、墙壁、地板等;软装就是指家具、床品、饰品等。”徐兴建表示。
“比如选择软装物件时,要结合当地风土民情,尽量使用带有当地特色的物品,融情于一砖一瓦。”徐兴建说,民宿的改建或翻新,一定要与当地环境相结合,符合当地的人文特色,因此要保护好当地的生态,包括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一个“失了根”的民宿,最终就沦为了一家普通旅店了。“民宿主的审美和素养的高低,也决定了民宿的成败。”
“民宿面向的消费人群属于中高收入家庭,本身是一个小圈子,民宿主需要有一定的人脉资源”,曾经作为房地产公司管理层的徐兴建介绍,目前他在延庆3个村子经营着10家民宿,大多不接散客,以包院的形式为主,主要消费群体有三类。“一类是带孩子来郊区游玩的年轻父母,一类是年轻住客的朋友聚会,还有就是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内部会议,都会选择郊区风景优美、舒适安静的高端民宿。”
在投入资金方面,多数村民也会捉襟见肘。“以京郊为例,宅院大多在二三百平方米,每个院子光装修至少需要80万元到90万元,这还不算运营和营销成本以及员工工资”,徐兴建说,“外来投资商还需要租宅院,根据院子位置和房屋等情况不同,每年3万-5万租金不等”。
徐兴建的团队已经签约了20处宅院,除开业的这10家,其他院子尚未装修。“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形成联动,如果接到客人多的大团,可以分散住开,也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徐兴建说,“我们签约期都为20年,一处宅子年租金在3万上下,分四次缴租,一次性预先缴纳今后五年的租金。”
记者与徐兴建算起账,不算别的,仅仅租下这20个院子,提前缴纳的租金就要300万。
“我们普通农民可没有这样的财力,就自家院子一处都改造不起”,樊丽萍说道,“就算我们去四处借钱,以后能不能赚回来还不知道呢,家里老人也跟着担心,全家都会有压力”。
回归后的困扰
由于民宿的进入门槛较高,直接由村民自营的很少。“都说北京民宿看怀柔,怀柔民宿看渤海,就渤海镇上百家民宿来说,由当地村民开的不超过10家。”渤海镇四渡河村民黄欢,是最早一批回乡创业的80后青年。
2012年曾在市里做广告行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四渡河,利用自家的30亩地开起了一家集采摘、食、宿一体的农家院。赚得第一桶金后,2015年,他又将自家老宅改造成了高端民宿。黄欢介绍,除了这两处外,他还在另建两处院子,一处租他们本村的空院,一处在不远的北沟村。

黄欢说,民宿的装修设计要有特色。李谦锋 摄
“刚开始辞职回家创业,父母还是很担心的,包括现在投资那么多钱开民宿的,大多还是年轻人。”黄欢说,“老人的观念比较传统,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更重要的是缺少人脉资源”。
“能够消费高端民宿的,还是中高收入群体”,黄欢向记者透露,为了多争取一些客源,他的民宿拉来了近10位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的合伙人。
与黄欢一样,渤海镇马道峪村的曹阳也是回乡创业青年。曾在外企做过6年营销的他告诉记者,2015年开始,他利用周末在自家院子,尝试经营民宿。由于生意不错,去年他辞掉工作,专职当起了民宿主。目前他的民宿正在营业的有两家,今年他又租了村里老乡一处空宅,正在建一个拥有3间客房的小院。
当地村民曹阳说,这是他第三处院子,院子盖好后会有三间客房。
“之前在市里上班,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选择回乡创业,在老家就能挣钱,父母年纪大了,还可以守在他们身边。”曹阳说,也希望通过他的身体力行,让乡亲们看到在家乡也可以有发展。
一个汉唐风格的小院,一口知青磨豆腐的老水井,配上青砖、棕红门窗和原木的家具,形成了眼前这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民宿。“其实现在很多家民宿不能称之为民宿,乡村精品酒店这个名字可能会更贴切”,黄欢介绍,真正的民宿,有别于标准酒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宿主人跟住客之间的深度互动,让住客体验民宿主的生活。但目前,很多民宿直接交由管家或其他工作人员打理,平时根本见不到民宿主,“这样的情况能占到总数的一半”。
民宿还要升级,门槛将再度加高
高昂的升级代价,农户单打独斗很难完成转型,而这场升级运动,在北京有政策推动与村集体主动承接,这进一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农家院或者说“农家乐”开始大面积消失。
在怀柔中榆树店村,大批民俗户在五月份停业改造,八月份将以新面孔恢复营业。这个深山村的改造动力,源于去年的一份文件——《怀柔区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奖励办法(试行)》。根据要求,建成的民宿验收达标后,金宿级民宿将一次性获得奖励12万元,银宿级的奖金是10万元。五星级民俗村最高可一次性获得奖励500万元。
奖励办法立竿见影,中榆树店村随之迎来自2011年全村产业转型为民俗接待以来的首次升级改造。今年的这次升级改造,大部分民俗户都将从4星升级为5星,其中有十余户将改造成高端民宿。除了政策资金支持,村里有专门的合作社进行组织,这轮升级还有专业民宿管理公司介入,开工前,村里甚至还组织村民开会,不允许找后账,打造精品民宿全凭自愿。
那么,民宿这么火热,在北京到底有多少家民宿?实际上,作为这几年才兴起的新兴业态,市级层面甚至对民宿数字没有精细统计。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缺少民宿领域管理体制,对于民宿数量无法做到细分统计,“但了解到民宿数量在攀升”。目前,《北京市民宿管理规范》尚未出台,相关制度标准正在制定。
实际上,当市场开始成形,自发的约束与基层的监管已经开始筹划与推出。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采访了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爱娟,她表示,“延庆的民宿发展史其实只有三年,但这三年发展很快。2017年底区内民宿11家50处宅院,2018年底为27家130处宅院,现在已有55家230处宅院,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涨”。
郑爱娟介绍,2018年由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导,区内民宿主组成了“延庆区民宿联盟”,并共同签署《文明经营公约》,防止出现恶性竞争。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联合民宿联盟,制定了《延庆区乡村民宿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民宿产业发展,对民宿经营进行行业监管。
“大概是情怀因素或觉得投资民宿有利可图,从2017年起,投资商开始进入民宿领域,民宿数量也呈井喷式上升”,黄欢和曹阳如此表示。数量增多,导致竞争激烈,今后是否会降低服务标准打起价格战,导致民宿再步农家院的后尘,则是不少经营者的心中隐忧。
“民宿是比较个性化的产业,消费群体有限,加上成本回收较慢,销售和运营成本压力很大。目前,北京民宿的数量还在攀升,虽然还未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但投资商们已经开始思考新一轮升级了”。至于怎样升级,徐兴建表示南方已有做得较好的模式,目前他们还在考察中,大体方向是朝着乡村文旅综合体发展,具体运营模式还不方便透露。
对于升级的时间,“预计今后一两年”,徐兴建说,“今后进入门槛将会更高,投资额也会更多,仅仅拥有一两个院子的小民宿主的生存压力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