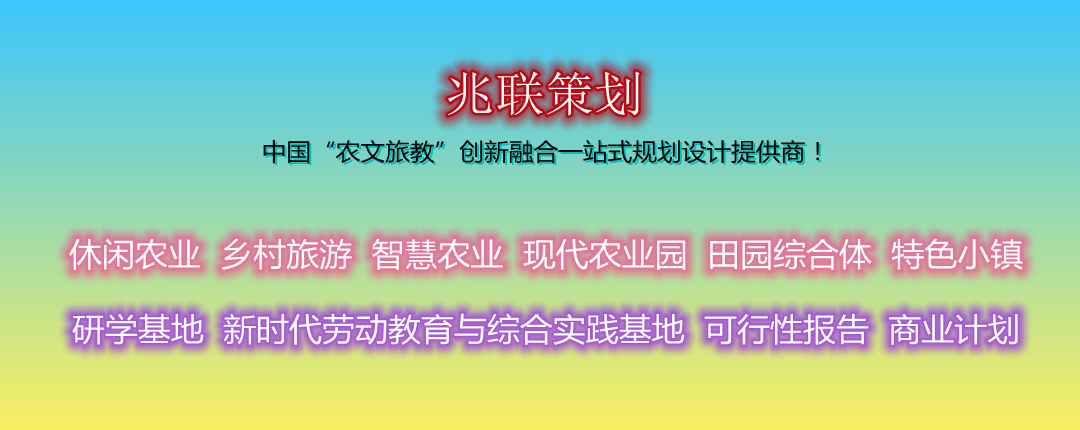自从有了点年纪,就总是喜欢回老家。伫立在村后坡头,闭上眼睛静听鸟儿啾啾鸣叫,贪婪地吸吮晨雾暮烟的味道。可是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的我们,对于家来说,永远只是一个过客。每次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来不及转身做深情地凝望。

我的老家蓝田县九间房镇街子村位于关中平原东南部,秦岭的伟岸雄奇和灞水的悠远绵长,以及众多的人文古迹,造就了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魅力。村子距离蓝田县城20公里,距离西安市区60公里。祖祖辈辈都以种养为生,那里水土肥美,风景秀丽,曾是周边不少小村庄的人仰慕的地方。

据村里老人讲,明洪武年间我家祖辈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世代在此耕种,后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加,又因人口居住集中,自然形成街道,是陕南特产、西安商品南北交流的必经之地,以此而得名靳家街,又称“靳家村”,解放后称街子村。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故居就坐落于村后坡上。村子对面王顺山巍峨挺拔;蓝田猿人遗址公王岭隔河相望;灞河像一条玉带与西商高速高架桥相互牵手蜿蜒向西流过;东面的歪嘴崖在夕阳的余晖下像亭亭玉立的美少女显得愈发婀娜多姿;北面横岭遥望。

毋庸置疑,时代的巨大变革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加剧让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乡村的纹理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故乡的记忆也在渐消亡。对此我们却好像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几天前的一次乡党聚会,让身处古城西安的几位乡党感慨万千,村里的磨盘,石槽,石板桥,果园,饲养室成了聊天的主题。儿时的时光仿佛回到了跟前。召集儿时伙伴相聚转眼间显得很是迫切。几个人迅速翻开手机通信录,相互联系县城工作的乡党,定好时间和地点,期待新的聚会。
蓝田聚会,大家如约而至,话题依旧绕不开村里的家长里短。

“街子村人杰地灵没有闷怂”成了忆往昔的开始!
小时候成群结队穿梭其间光洁的小路,如今已经杂草丛生,难掩萧条。街巷里,熟悉的邻家个个人去房空。一个略显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声逐渐远去……
村里的街巷记得小时候是我们男孩子滚铁环,女孩子踢毽子、丢沙包的聚集地,仿佛还可以听得见邻家女孩银铃般的笑声。村子南边的磨坊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曾经整天机器轰鸣,人车络绎。那时候在磨面机的响声里,人们互相说话都要趴在耳朵上大声的吼叫。

每一个院落,一旦入了镜头,都是一副溢满沧桑感的画卷。
高大的核桃树,见证着老家人们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沧桑。不管我们在与不在,它仍然会日夜守候。
村里过去有一个涝池,积攒了满满当当的天雨水。小时候一伙儿小淘气曾经脱了光屁股骑根大木头在水面上划船。有时候还会故意把谁家的猪赶到池塘里欣喜的观赏它游泳的姿态。涝池边的路上是妇女们洗衣服的地方,也是男孩子摔泥盆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总是比谁摔的声音大,谁溅的泥水多,所以没少挨那些父母的责骂。现在这里已建起了新房,主人一家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回家。但仿佛仍然可以听到嘈杂的熟悉的乡音,余音袅袅,挥之不去……
村子的老学校,曾经多少人在这里奠定了走出农村的基础。每一户充满童年回忆的老屋都已物是人非,院子里杂草丛生,只有那散乱废弃的物品仿佛在诉说主人的曾经。房子背墙上的标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就像关于儿时,关于故乡的所有记忆,无意间就渐行渐远,记忆模糊。

过去夏收时节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大场,现在早已经弃用。空荡荡的,仿佛在向每一个人诉说着它曾经的历史悠远。
过去全村人用水担去村东井里挑水,老年人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年轻人你追我赶气喘吁吁。每到早晚,这条路上人来人往,水担铁钩和铁桶畔子摩擦发出尖利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萦萦绕绕,绵延数小时而不歇息。
老树,荒草,老人,磨盘。所有的过往都已经成为历史,让我们把美好的记忆永远珍藏心底。

“ 你家门前的山坡上,又开满了野花,多想摘一朵戴在你乌黑的头发。就像两小无猜的我们玩儿的过家家。捏上一个泥娃娃,我当爹来你当妈。。。。”这首充满凄凉的歌曲回忆过去又是那么的恰切!
小时候,故乡的芳草,树木,野花,和村头的大树以及晚霞里树下的饭后闲聊,都似剪影,在不经意间随时出现在眼前。岁月是条河,我们在这头,故乡在那头,她终将会成为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年少。然而,那一泓乡情与怀念却在炊烟袅袅中涌动,融入我们的血脉,带着最后一丝暖意,慢慢侵入黄昏。 就像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老屋,终将成为一幅幅斑驳的油彩画,挂在沧桑的记忆里,慢慢泛黄却永不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