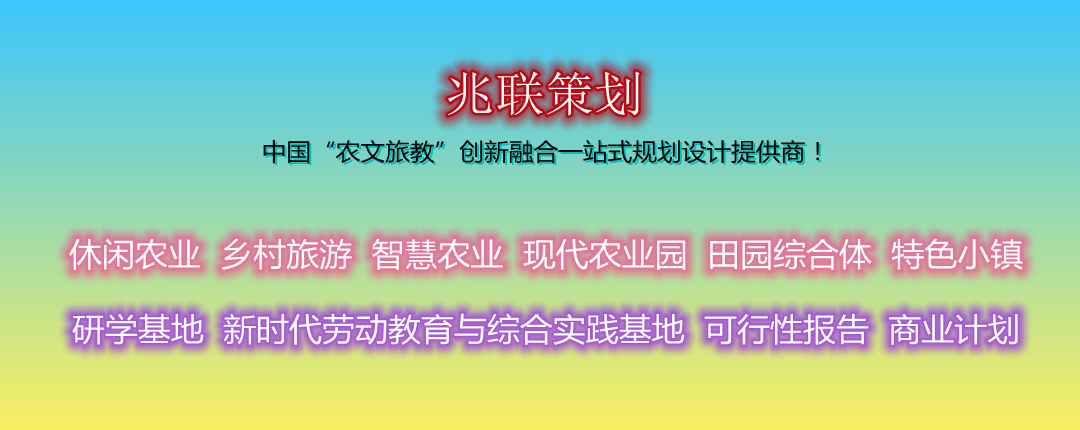我有一个农场,那里有地有菜,有河有鱼,有草有羊,有篝火有晚会,有野兔有野猪,能唱歌能跳舞,能吹牛能追女孩子,还有绵绵的情话和星星……
——《我有一个农场》。

01 我有一个农场
都市生活忙碌又不规律,工作长年累月朝九晚六,灯红酒绿撑大的是无尽的欲望,繁华背后是无数身心疲惫的躯壳和空虚寂寞的灵魂。
很多人都有改变生活方式的愿望,却奈何不知从何做起,于是田园生活成为都市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诗和远方”。
春暖花开,盛夏凉风,午后温暖而灿烂的阳光,嫩得发油、发亮的生机勃勃的蔬菜叶子,生猛奔跑的家禽……树荫下、吊床中,沏一壶茶,抱一本书,一切都那么宁静、美好,令人向往。
我有一个农场,很多前来作客的朋友都会感叹:“真羡慕你们的生活!我也有一个田园梦,只是被工作和家庭束缚着,没有机会去实现。”
以前我会暗暗耻笑那些空喊口号、没有勇气踏出第一步却诸多借口的人,后来才明白,那一步真的不是空有满腔热诚便能迈得出去的。
因为但凡世间令人向往的生活,有多美好,就有多艰难。
《我有一个农场》这本书就是写一个曾经在城市打拼的女子,毅然放弃城市生活,回归乡野耕地种菜、卖菜。
作者刘跃明就是这个女子,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农场创始人,与很多中途“转行”的归农人不同,她确实本来就对乡野和农业深感兴趣,就连大学所读的专业也是生物系。
她曾经跟大部分人一样,作为一个在城市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日没夜地工作赚钱,后来身心疲惫,回到家乡开了一个农场,从此过上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
以月亮为伴,跟星星说话,还时常与朋友聚会、钓鱼、野游,起篝火,烤全羊……所有你能想到的美好时光,在那个农场通通都可以实现。
02 超越传统,打造无污染生态农场
作者当年从秋天有了“回家做农场”的想法,再花了几乎半年时间去调研、学习、搜索资讯、实地考察、检测土壤、评估,直到来年春天才收拾行装,奔赴老家那片农田,正式开荒。
因为她要做的不是普通的传统农场,而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场。
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是这个世纪才爆发的严峻问题,但在较早工农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比如欧美、日本等,早就发生过食品安全问题。因此,他们早已意识到化学农业的危害和不可持续性,于是,生态农业被提上了日程。
这种农业模式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出的安全性,不但在种植过程中不用任何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物质,对土壤更是经过科学检测和筛选,确保各种指标及格才投入使用。
所谓原生态,就是遵循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原则,尽量按季节种植、露天种植,让作物通过吸收日月精华和历经自然风霜雪雨,天然地增强抗病、抗虫能力,从而保护环境和土壤的可持续发展。
不用化肥,作物当然不及使用化肥的生长得快和肥大;不用农药,杂草、虫害只能靠人工去除。这些都大大增加成本,却减少产量,从而使菜价比一般菜价高出一大截。
因此,传统的经营模式行不通,所以作者把经营模式定位为“CSA”模式。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的英文简称,它起源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瑞士、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是消费者与农民之间达成供需协议,以消费者提前支付费用,农民按需生产,为消费者提供应季农产品的经营模式。这些消费者希望寻找安全的食物,而这些农民则专门生产安全、健康的有机食品。
CSA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场经营者摆脱工业化农业生产,避免用有害健康的农药、化肥去追求高产量,从而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经营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盛行,但在我国却仅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03 回归传统,天人合一
整本书,作者用了大半的篇幅去描述开荒、耕种、收成的全过程,以及各个季节的产物和特定状况。原以为知识分子回归农田,理念超前,经营模式时髦,必定会配上高科技的种植技术或新鲜的耕种模式,谁知通篇读下来,却颠覆了我的预想。
这个农场从翻地、播种、育苗、去虫、除草,甚至堆肥,都运用着农耕时代最传统、最天然的耕作模式。
现代农民一看到病虫害,就马上用农药来镇压,导致土质和生态日益受损,土地越来越不适合种植,于是农民每隔几年就要换个地方耕作。
其实大自然是很神奇的,每一种病虫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克星,比如草木灰能杀菌消毒,防止植株伤口感染腐烂,还能防地下害虫,所以旧时人们常常用它来伴土豆种植。
现代有机农场很流行温室种植和无土栽培,但作者始终觉得,直接种植在大地上的蔬菜,晒过太阳和月亮,被朝露滋润过,被风雨拍击过,植株才更茁壮,叶片也更厚实浓绿,而瓜菜本身特有的味道才更浓郁。
所以她一直坚持采用土地耕种的方式,让每棵青菜、每个瓜果都与大地相连,保持它们原本独特的味道。
她还严格按照24节气的规律去布置耕作。
24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精华,古时人们通过观测一年中天文、气象、气候、物候等自然规律的变化,所形成的一套农耕与大自然节律关系的知识体系。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古时,人们就是通过24节气去估算气候的变化,以此判断农时,安排劳作。它可谓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精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业讲究天人合一。不管人类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人永远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倚仗着自然而生存,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都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怪不得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写道:“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现在我偶尔还会看到母亲翻阅日历,按节令衡量播种的日子。估计现在能运用这种智慧的,就只剩下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了。我们这一代被科技豢养得太久,农业工业化早就使我们遗忘了祖辈积累下来的智慧,当某天有人又把它们运用起来,人们反而感到诧异和质疑。
“最困难的是,生态农业如今还是非主流农业,可以找到的具有实战经验的专家、老师并不多,尤其我们要给客户搭配菜篮,需要同时种植很多品种,而且要保证连续性,就更不容易。所以,我们也需要努力学习、努力摸索。”
所以,当我读到书中这一段的时候,我竟不知道,人类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04 做农业,有多美好,就有多艰难
田间漫步,呼吸着清新无污染的空气,盛夏凉风下捧着书昏昏欲睡,世间美好得就像在野地里撒一泡尿都会变成一道彩虹。
尽管作者从头到尾都表达着对农业和乡土的热爱,字里行间尽是诗情画意,从耕种工事和无数小插曲中,却透露着这令人向往的生活背后所倾注的艰辛付出。
做农业不是摆拍,更不是度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仅仅是一种即兴的浪漫情怀,农业日常更多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先不说农业本身就是“三高一长”的行业,即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和周期长,就算掌握了耕种技术,若不是巨额遗产继承人,也未必能承受得住农耕的那份辛苦。
比如在霜降前后要密切监察天气,“浓霜猛太阳”,长得再好的瓜果,霜一打上就冻坏了,没法吃,所以一定要抢在“霜降”前抢回来。
有一年,作者的农场就特别狼狈,因为一直忙着其它事务,瓜田里的冬瓜、南瓜到霜降时还没收,直到傍晚听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霜冻,才急忙召集全体员工加班,漏夜抢收。
而夏季是暴风雨的季节,老天爷一发威,来个10年、2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被雨水泡过一夜的蔬菜基本就报废了。若雨水不断,那些根系作物如红薯、香芋、土豆等,也基本没用了。如此,小半年的劳动也就白费了。
天晴一到,心再酸,也得马上卷起裤管袖子投入新一轮抢种,刻不容缓。
农场经常要搭建棚架,冬天保温,夏天遮阴。但倘若一阵无理取闹的阴风突然而至吹翻棚架,还压坏一地蔬菜,你发脾气也没用,唯有默默收拾残架,重新再来。
作者形容,种地就是“伺候生命的过程”,劳心也劳力,得时刻做好全面准备。
如果以为蔬菜瓜果健康得发油、发亮就可以高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生机盎然的景象并不是光看着就能饱肚的,还得想办法以一个好价钱卖出去,以换取收支平衡或盈利。
这就涉及到经营,一旦成为经营,就牵涉到一个行业、一门生意,就需要考虑到一系列问题。如作者所言:
“不管是一个农民种着一亩地,还是一个团队、一个公司操作着几百上千亩地,都一样,只要涉及到生产、管理、技术、财务、营销、市场等各个环节,那就变成一门生意。”
诗意不得,任性不起,因为做农业,有多美好,就有多艰难。
写在最后
大概每个怀有田园梦的人,都向往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中宁静、纯粹的生活。
以前我不明白,既然瓦尔登湖的生活如此美好,给他如此丰沛的灵感和启迪,为何梭罗只待了两年就离开?
后来在《认知突围》中读到关于人生那部分,作者说:
“人生的最大意义在于体验,总是体验重复和相似的风景,其实在人生的时间利用率上是吃亏的。”
他说,我们真正的目的应该在于“体验”,去丰富自己的时间经历。举个登山的例子,在山脚下和山顶上所看到的风景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努力去体验山顶上的风景,却不要把登顶作为目的,否则这一生就不得不为守住这个山顶而努力。
我有点理解为何梭罗要离开瓦尔登湖,他大概觉得没必要把全部生命花在一种活法上吧,他在《瓦尔登湖》最后写道:
只要注入美好的理想,前景便会一片光明。如果我们时常生活在“当下”,对任何机遇都能善加利用,就像青草坦然接受一小滴雨露的恩泽一样;不错失良机后再扼腕叹息,不把时间浪费在埋怨上,也不把前两者认为是自己应尽的职责,那我们就是幸福的人了。
他是否幸福,跟他是否在瓦尔登湖无关,只跟他心中是否有“瓦尔登湖”有关。
同样的,我们内心是否真的宁静,跟我们是否在乡村、在农场无关,而与我们心中是否有那座幽静而灿烂的“农场”相关。
只有真正热爱当下的生活,随时随地都有感受宁静的能力,当有天真有机会体验乡间生活,才有能力领略个中恬静和美好。否则,给你再诗情画意的农场,很快你就会厌倦,甚至烦透种种不便和繁琐杂务,而那时,“诗和远方”只会变成“一地鸡毛”。
农场生活很美好,但经营一个农场,实际上比在都市打拼还要艰苦,若没有赤诚的热爱、扎实的专业基底、吃苦耐劳的毅力,以及乐观的天性,是很难体验到当中乐趣的。
尽管一切都不容易,而踏出第一步确实很难,但我还是想像歌德那样说:
“不管你能做什么,或者梦想你能做什么,开始去做吧。”